
前几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退休的老法官打来电话,感谢我斡旋化解他儿子公司的法律纠纷,闲聊中说到了律师的社会价值。我客气地说如果要感谢,还应该感谢他的先祖沈家本(这位老法官是沈家本五世孙)。沈公在清末将西方文化下的律师制度移植到古老的中国土地上,今天的中国才会有律师这个职业,律师才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1905年,“清末立宪”中沈家本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起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华法系的固有惯例,但该草案未被清廷接受。沈家本希望通过立宪造法挽救清王朝的设想彻底落空,他没能成为“中兴名臣”,相反他的名字于6年后出现在隆裕太后宣布的《宣统皇帝退位诏书》附签的十一位内阁大臣中,成为清朝灭亡的“见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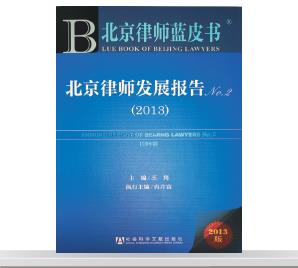
2020年是律师制度恢复41周年,在2009年北京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年时,市律协作出了每两年出版一卷《北京律师蓝皮书》的决定。2011年,第一卷蓝皮书出版,我是该书的两位主编之一,并亲自编撰了《北京律师发展历程1949-2009》一章。时至今日,第五卷蓝皮书即将出版,今天的北京律师行业比10年前又有了显著的进步。回顾当年编写《发展历程》大事记的过程,还是有很多的感慨。
回顾历史是发展的基础
大事记收集编辑了新中国成立后1949-2009年律师行业的多数重大事件,以此勾勒出1949-1979年前30年间的律师制度的辛酸经历和1979-2009年后30年律师制度的恢复发展历程。
虽然西方社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律师,但中国律师制度到2012年才有百年历史。尽管大清王朝没有颁布沈家本起草的法案,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当年就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明确创立了律师制度,律师在社会上开始正式出现。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短短37年间,律师群体虽然极其弱小,但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还是令人眼前一亮,“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施洋律师为维护工人利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七君子事件”爆发后律师们的抗争等等,都在中国律师制度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国民政府还颁布了第一部《中华民国律师法》。
新中国建立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旧法统,旧的律师制度也同时被废止,因此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律师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无暇顾及。1956年,根据《五四宪法》第76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司法部、公安部发布《关于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问题的联合通知》 ,规定了“人民律师参加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活动”,使得人民律师成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方主体正式出现。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截至1957年年中,全国建立了19个律师协会,800多个法律顾问处,专职律师2500多人,兼职律师300多人。可是制度、协会、机构、人员的存在,并不能表明律师制度已经建立;相反,在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为坏人辩护”的原罪使得1/3的律师被打成“右派”,整个律师队伍噤若寒蝉。1959年,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司法部被撤消,律师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但律师执业活动已停顿。“文革”爆发后,律师制度被正式取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战略方针后,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辩护制度在国家法制中的地位。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作了专章规定,重新明确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因此,1979年成为律师制度恢复的元年,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
回顾历史是为了说明律师制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全国律师队伍发展到五十万之众的成果。
记录历史才能总结经验
编写《北京律师蓝皮书》的大事记是一个非常艰辛和痛苦的过程,资料的极度缺乏和散失,一些重大事件的记录语焉不详或前后矛盾,给撰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自己深知编辑《大事记》责任重大,生怕遗漏重大事件,这使得我在撰写过程中翻遍已有的材料,到处搜集相关文章;往往整理了一些内容,因为不满意又重起炉灶……
北京律师制度的恢复是中国律师制度重建的重要内容,律师制度中的很多改革试点、新制度的探索和完善、行业引领的焦点问题都是北京律师行业先行先试的,也是写大事记的难点。有些改革是司法部推动,有些是北京律师管理经验的总结。如:1985年,北京市司法局开始对律师事务所的经费管理进行改革,将过去律师事务所作为事业单位,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僵化体制,根据事务所运行的实际情况改革为三种类型,即全额拨款、统收统支,独立核算、差额补助与自收自支,极大激励了律师工作的积极性,成为吸收人才、扩大队伍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1995年中办、国办转发《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两不四自”后,北京率先审批设立了几家合伙律师事务所;并在同年第四次北京律师代表大会中选举出由执业律师组成的理事会,第一次由执业律师担任律师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
律师制度恢复30年的进程,基本上是围绕着律师改革的脉络进行的,这里面是几代人的奋斗成果,虽然大事记不宜突出个人,但主管机关的工作领导、行业协会的不懈努力、律师事务所的发奋有为以及挺立潮头的优秀律师,都是我们大事记中健壮的筋骨和流淌的血液,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北京律师的发展朝气蓬勃,引领了全国律师行业。
把握历史规律谋求发展
编写大事记固然是为了铭记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展望未来。纵观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律师制度的演化,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发端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律师制度,到市场经济的今天行业全面兴盛,我们的律师制度有几个特点:第一,律师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但包括律师制度本身,也包括法治环境的转型。律师制度恢复之初,整个社会更关注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律师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律师的界限,唯恐我们的律师变成西方社会的自由职业者,因而固步自封。但随着改革开放,律师服务社会、服务公民、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大,律师队伍的发展逐步打破了过去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第二,尊重律师行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四十年来,每一次律师制度的重大改革都催生了行业的迅猛发展,改革就是解除束缚在律师制度上的条条框框,使之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从而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律师行业的良性发展是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实现的。行业自律到行业自治仍然是律师行业 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第四,律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也会因为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社会治理、社会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
在《北京律师蓝皮书》第五卷即将出版之际,北京律师截至2019年年底已经突破35000人,2700多家律师事务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北京律师行业的发展应当有新的规划,我认为未来的发展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在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完善制度方面继续努力。